时间: 2021-08-03 10:05:50 人气: 11 评论: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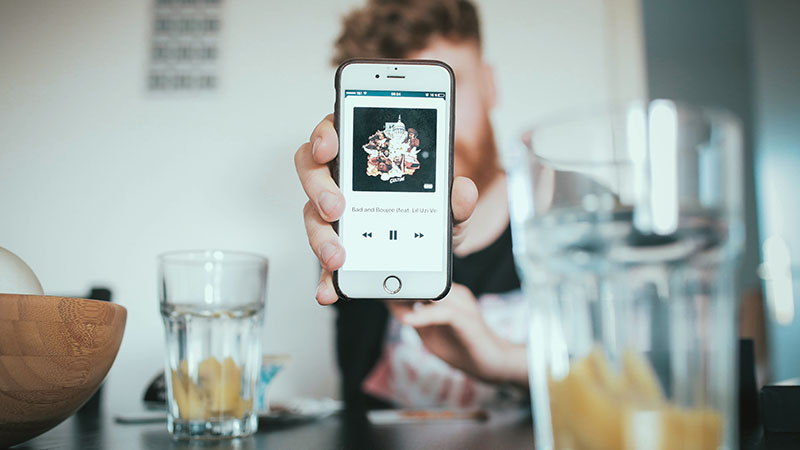
1999年,数字革命还处于初期阶段,能运用互联网做到的事情非常有限,Anne Helen Petersen 在本文中讲述了他当时身为大学生的她和她的朋友们是如何度过那段青葱岁月。而通过与如今网络世界的对比,她又获得了什么感悟?互联网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失去了些什么?
当我1999年开始上大学时,数字革命还处于尴尬的初期阶段。而这种尴尬的情况给予了人们许多的意外收获——幸福的无知。
![]()
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有一个人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他住在楼上,整个宿舍里唯一的单身者。他的头发是栗色的,手臂肌肉像攀岩者的一样粗壮。他是我初到校园时看到的第一个让我目不转睛的人,当时他帮助别人在墙上挂挂毯。当然:当时是1999年。
他的宿舍里摆放着一长排的CD,他还教我从200人宿舍中共享以太网连接的音乐库中下载的钢琴的音轨。但他从来都不接宿舍里的电话。他在AOL Instant Messenger上的用户名就是这个软件名字的缩写(ATM)加上他的出生年份(80)。他长期在线但却从来都不聊天,因此我觉得他的**色小人头像总是在耍我。
唯一能得到他回复的方法就是发邮件,我们通过远程登录在校园里收发邮件。尽管我总想要接到邮件但实际上收到的数量并不多。这种发邮件的方式非常简单粗暴,只用一个字母就可以完成删除、转发和回复的指令,不能添加图**,不能使用字体加粗、斜体或下划线等功能。该软件最好的功能FINGER也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你需要在远程登录的主页上打字输入6个字母的个人用户名(姓的最后4个字母+名字的首字母+中间名的首字母)。然后**弹出也可能不**弹出一个单相思大学生最想要的界面:日期,时间,上一次登录的地点。
事实上,如果有人打开那封你精心编写但通常只有3句话的电子邮件的话,这可以说是一种跟踪行为。但Finger不仅仅使那些处于暗恋的人受益;它还可以帮助你找出对方所在的计算机实验室,搞清楚对方放假后有没有回到学校。比如我当时一位大三的朋友,他发现和他约**的人称自己住在泰国的海滩上,然而实际上这个人的IP地址却显示蒙大拿州农村的某个地方。
Finger是当前如发短信、阅读回执以及GPS跟踪这些完全构成我们日常互动的科技的先驱。1999年就像是陷入僵局的一年,有足够的数字工具去影响——而不是改变——我们对关系、互动或者友谊的模拟理解。
1999年,互联网还未成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我们还没能用自己的方式上网,即我们在数字世界的行为(发邮件,登录非常慢的网页)并没有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线下和线上的身份还没有融合。
这些新生的数字技术:在宿舍里有互联网,甚至还有以太网,但却没有Wi-Fi——这就意味着台式机必须保持有线连接的状态才能上网。你可以使用Napster和文件分享,但这种方式很慢还伴随着法律风险;当然还有AIM和ICQ,但这些必须坐在电脑前才能使用;网站永远都在加载中;上网浏览的距离变短了,却更难以操控;手机非常稀有,尤其在公共场所;无线电话也仍然需要电话卡;DVD则被搁置在VHS磁带的旁边;而Winamp播放器和刻录的CD混合磁带却与实际的CD混合。
没有社交媒体,或者手机摄像头——更别说数码相机或录像机了。没有谷歌地图,甚至连谷歌都还没问世。计算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让生活变得更便利,但也并没有使发生实质性的改变。Finger能帮助我查到一些东西,却还不具备查到一切我想知道的信息的能力。
这种大众连接性很有趣很神奇,就像你珍爱的一个新玩具,但你也有可能随时将它丢在一旁。这个时期,包括我在内的一小部分人都处于上大学的阶段:一段最能体验(怀念)连接的时期。要说我们这群经历过这种融合的人不属于任何一代人也是说得过去的。算作X一代太年轻,而作为千禧一代又太老了,因此我们通常被称为Catalano一代或者Oregon Trail一代,沉迷于还未完全成为真正互联网的互联网早期阶段。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沉迷是病态的。如果你周末的时候想找你的朋友或其他人,亦或是想要更多的啤酒以及一大碟玉米**,你只要走出去找就可以了。然而我们却**一头栽进24小时开放的计算机实验室里来检查邮件。而该邮件则发自某个被放在地下室里总是在运行却没有密码保护的网关。
或者你也可以在你门上的白板上写下你今日的行程——“4-6点:图书馆;6-8点:看电影;8点后:在Phi家开派对”——很快你的门板就**被别人用从楼下大厅的门上偷来的彩色标记笔,草草地写上“Hi, 我半夜的时候很想你”。
让人们在同一时间聚集到同一个地方最好的办法就是给Listserv(邮件用户清单服务)写邮件。Listserv可以传达到所有宿舍、班级乃至全校。我所就读的大学相对较小(差不多1200人)。但有这么多人能收到你的失物招领邮件、激昂的政治演说以及一名开着红色陆地巡游车的女生碾过你的飞碟这样的醉酒话,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话题**增多,且种类多种多样,而这也成为了今日很多线上交流的准则。在举行完一年一度的啤酒英里比赛后,几十人向全校发布了失物寻回的邮件,而有一群喝醉的人则用朋友的账号发布了这样一条邮件:“我在比赛中丢失了处女之身,有谁看到吗?”所有人,包括这个女孩都哄堂大笑。这显然违反了秩序,但它却可以在朋友和同学之间流传。
Listserv成为发布派对行程的工具,但大部分聚**都是不经意间就举办的。我的一位朋友曾经给宿舍里其余5个人买了一个酒桶,但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等着别人找她开派对,结果真的就开了派对。假装在走廊上找一个人,你可以看到一群听着你喜欢的歌的人走进一间房,待上一个小时甚至一整晚,就像进了一个满是啤酒味的虫洞里。
在大学里只能听到数量很少的歌,因为音带的容量很小,而且只能重复播放。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地下室,在那儿玩或者看别人玩啤酒乒乓球。而只有两张CD是最带感的,一张是Dre’s 2001,另一张是Toby Keith and Tim McGraw的乡村音乐。在我们的家庭电脑里虽然有更多的选择,但公共场所仍然只能播放 CD。如果你的好朋友切歌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这首歌引起了她和她男朋友分手的回忆。
当时还没有Netflix,因此你得去图书馆借DVD并在派对的下半程听完,但也仅限于你有一台电脑或者DVD播放器的情况下。你们还可以一起挤在宿舍公共电视房间的地毯上,看朋友的妈妈寄来的录制了Ally McBeal全集的VHS。
今天,我们期望大学生能成为酷炫的媒体消费的先锋;但在过去,我们却是一个黑洞:带着我们带来的东西闲逛,却无法发现或增加任何新奇的东西。没有人有杂志;评论网站永远无法加载。没有社交媒体,我们只能在偏远的华盛顿郊区的其他人中展示我们有限的文化品味。
在那个时代,大家的时尚审美都是一样的。当时我们离网购出现的时间还差一年左右,因此大家的衣服都是从家里带来的,或者是在小小的幽闭的梅西百货那里买的,而买到的全是去年的款。一条短天鹅绒礼服被这么多的人穿着参加过这么多正式的舞**,甚至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条裙子到底是谁的。而唯一的证据就是用廉价破烂的配有双设置变焦镜头的Vivitars和Canons拍下的照**。我们把底**拿到Safeway然后等过几天照**洗好后再郑重地发给最好的朋友。
![]()
由左上方顺时针方向依次为:1)我们通常用于联系的方式;2)当时年少无知的果冻派对的照**;3)我的模拟宿舍;4)一张非常糟糕(也很经典)的自拍
每张照**都拍得非常谨慎:一群女孩儿把脸凑在一起拍下一张照**,而不是20次。自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没有人可以帮你调整拍摄的角度。如果你回看一系列自拍,你**发现大部分的照**都有瑕疵(红眼的,闭眼的,灯光有问题的),但我们**挑出最好看的一张贴在门上或墙上,又或者用相框裱起来。这就是在Facebook and Instagram出现,并能把照**调得更好看之前,我们寻找乐趣和维持社交联系的方式。
同样的,当有人做一些傻事,比如用一个旧床垫从二楼窗户“冲浪”,然后掉进灌木丛或者搞一个果子冻滑梯时不**有满屋子的iPhone手机录像。我们的轶事就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只有在场的人才**知道你在派对上有多好看,玩得有多尽兴。没有人**一直玩手机,**Twitter;没有人**给别人发短信约见面的地点;没有人**说“我们一**儿打电话确定我们的计划,”因为你**当场就做出计划并执行。那是一种直接的、当场的、当下的生活方式。
或者至少这是一些我想讲述给我们自己听的故事。我们这种直接的生活方式慢慢地被科技产品所渗透:2002年,一名朋友带着数码相机回到学校,拍下的数百张照**瞬间使我们的成就感变得所剩无几。我们知道不允许那些在我们房子里聚**或在门口闲逛的大一新生带手机的行为注定是一场失败的尝试。
缺乏与外界的联系只**加重文科学院,主要是白人文科学院的稀缺程度。人们参加主题为“白色垃圾”或“妓女和皮条客”这样的派对而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一面镜子来反映这些事,或者没有来自网友的责骂。这种感情导致我身边的女性朋友直到成为研究生才真正了解了女权主义和交集性;导致有人用朋友的账号发送“我在啤酒英里的活动中丢失了处女之身”这种邮件却没人鄙夷;导致有些人**越过伦理底线而发生性行为。
在那个向数字世界过渡的年代里,非白色人种和中产阶级的人想找到一所像我们这样的学校要面临更多困难。因此,我们学校**被人称为白人学校。当我们谈论到在校园发生的有关性别、性行为、种族、阶级和性侵犯这样的问题时,大家都将它们归为一些零碎的问题,而与压迫、排斥和权利这些系统性的问题无关。
持续的连接性可能**让人感到疲惫和分心,觉得生活总是充斥了各种事情,就像站在一个永无止境的气旋的入口。有时我**怀念那些日子——我所能知道的关于某人的上网记录就只有他们最后一次登陆的IP地址。我已经忘记了排队等火车、结账和看医生时自己静静思考的那种感觉。
当然,这些事情还是可以做到的。只需要一点意志力,而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却没能做到。我一点也不羡慕当今的学生有这么多分散注意力的事,他们集中精力于专业领域选修、测试和作业的竞争。但随着别人的观点、生活经历和意识形态对自己造成越来越多的干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变得更困难和更复杂。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大学不仅是弄清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的阶段,也是使自己的言行对周围的人和整个世界都产生真正影响的时期。在今天,只有那些有特权和足够权力的人才能承担起断绝连接的代价。
对我和我的朋友而言,1999年之所以是美好的,是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安全、不用考虑后果的世界里隐蔽得很好。我们是被选中的接受了人文教育的孩子,基本没有经历过挑战和自我拷问。
我很怀念远程登录,怀念Finger;我很怀念那个人,门上的白板,劣质的VHS磁带和打开一袋新照**时满怀期待的心情。但我却一点也不怀念只靠我自己看到和了解这个世界的感觉。
原文地址: www.buzzfeed.com
译者:廖晓敏
译文地址:http://36kr.com/p/5061915.html